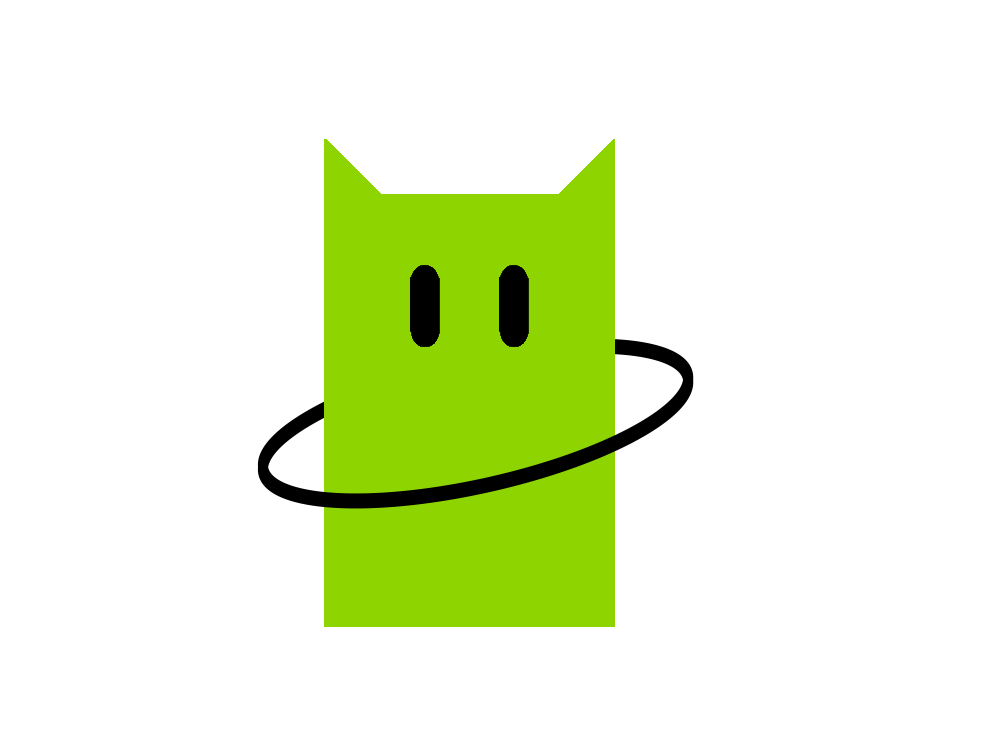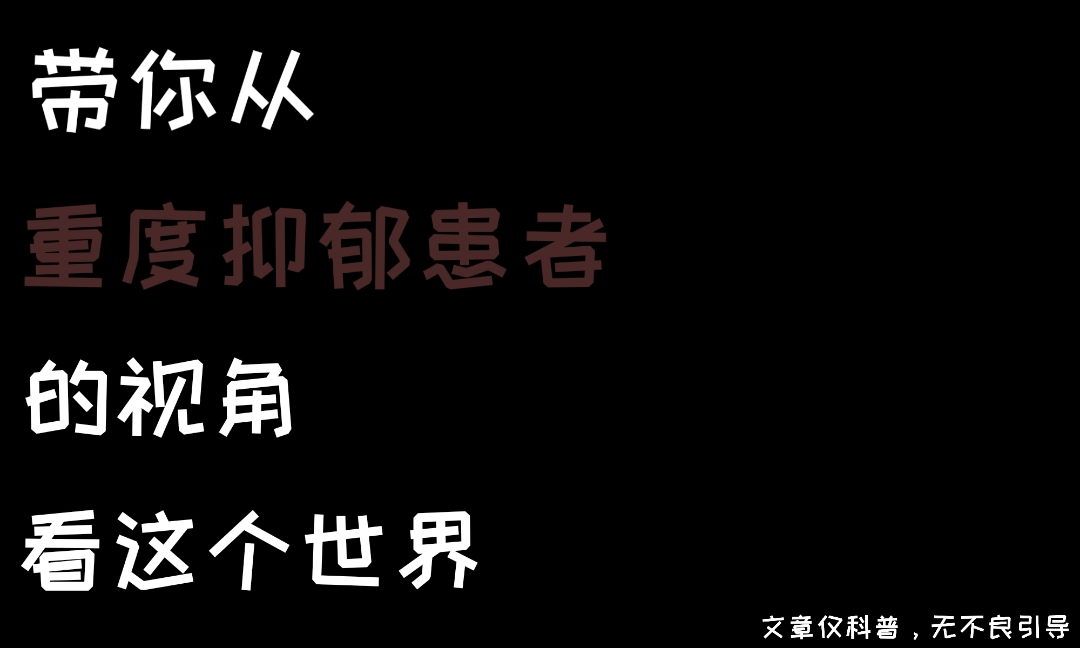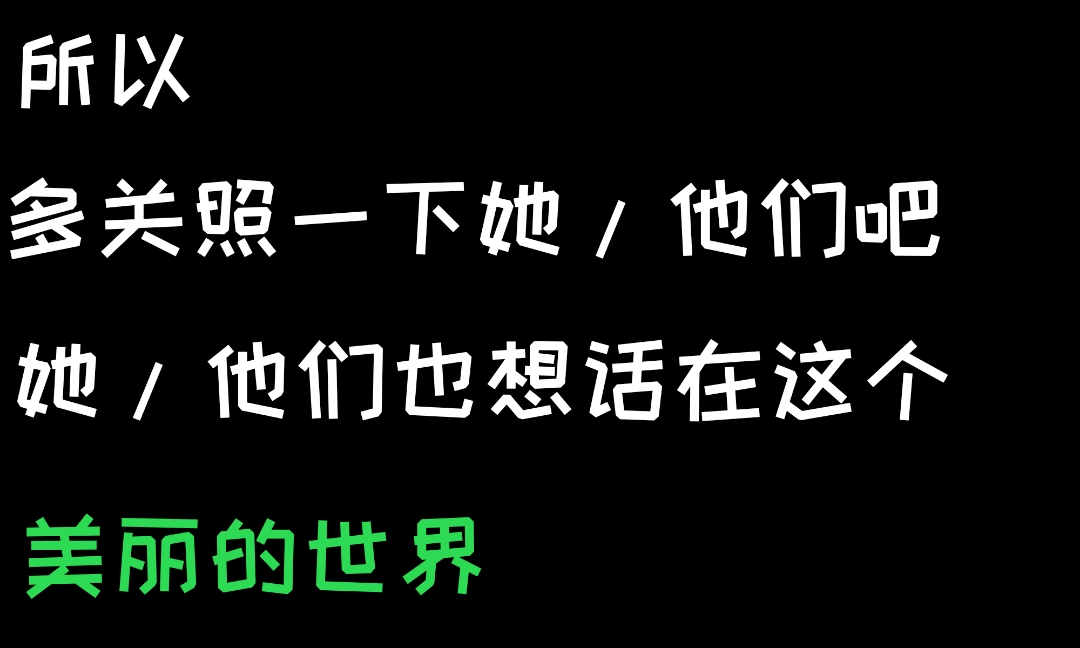今天是星期三,也可能是星期四,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。窗外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钻进来,像一把钝刀,缓慢地割着我的视网膜。我知道我应该起身拉开窗帘,让所谓的”美好的一天”开始,但我的四肢像是被灌了铅,又像是被无形的绳索绑在了这张床上。
床,这个应该带来休息和恢复的地方,现在成了我的牢笼。不是那种有着铁栅栏的牢笼,而是更加温柔的、几乎带着母性光辉的牢笼。它接纳我所有的重量,包容我所有的懒惰,不问我为什么不起床,不问我为什么不吃东西,不问我为什么连小便都要憋到最后一刻才蹒跚着去解决。它是唯一不会用疑问和期待压迫我的存在。
我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看。那条裂缝从我搬进来的第一天就在那里,像一个微笑,又像一道伤疤。有时候我会想象它慢慢扩大,整个天花板塌陷下来,把我埋在这片废墟之下。这个想法并不让我恐惧,反而带来一种奇怪的安慰——至少,那样我就有正当理由不动了。
手机在枕边震动了一下,是妈妈的短信:”今天感觉怎么样?记得吃药。”我盯着这条信息看了很久,手指悬停在屏幕上方,却打不出一个字的回复。说什么呢?说我还是那个样子?说药物让我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空壳?说谢谢她的关心但我真的不配?
最终我把手机翻过去,屏幕朝下,好像这样就能把那条信息、那份关心、那个期待都压碎在黑暗里。我知道这样做很残忍,妈妈只是担心我,但有时候关心感觉就像沙子,越多越让我窒息。他们想要我”好起来”,但他们不知道,”好起来”意味着要重新面对这个我无法理解的世界,意味着要重新戴上那个叫”正常”的面具,意味着要重新学会说谎——“我很好”、”今天不错”、”谢谢关心”。
厨房里传来冰箱的嗡嗡声,提醒着我那里还有食物。可能是昨天剩下的外卖,也可能是前天,或者大前天。时间在我的公寓里变得粘稠,像过期的蜂蜜,分不清昨天和上个星期的区别。我告诉自己要起来吃点东西,哪怕是一片面包,但”起来”这个动作需要调动的能量让我望而却步。不是懒惰,真的不是。如果你没经历过,你不会明白,那种连呼吸都需要刻意努力的疲惫,那种连眨眼都像举重一样的沉重。
我记得小时候学游泳,有一次不小心掉进了深水区。那种无法呼吸、四周都是水却没有一滴可以救命的感觉,和现在很像。只不过现在我没有挣扎,我知道没有人会来救我,也不值得别人冒险。我就这样沉在海底,看着水面上的世界继续运转,阳光透过海水变得扭曲而遥远。
窗帘缝隙里的光渐渐变得刺眼,我翻了个身,背对着窗户。这个动作消耗了我今天大部分的”社交能量”储备。是的,即使是一个人独处,我也有社交能量,只不过消耗的对象是我自己。每一个决定,每一个动作,每一个想法,都像是在和内心的某个部分对话,而那个部分总是用最尖锐的声音回应:”你做不好”、”你不行”、”你活该”。
有时候我会想,如果抑郁有实体,它会是什么样子?可能是一团黑色的雾气,不,不是那种戏剧化的黑色,而是那种洗过太多次的旧T恤的灰色,带着体温和汗水的味道。它会缠绕在我的脚踝上,顺着血管慢慢往上爬,最后定居在胸腔里,像一块永远捂不热的冰。它不说话,但它会让我听到的所有声音都经过它的过滤,结果就是我听到的每一个字都带着回声:”失败——败——“、”没用——用——“、”消失——失——“。
我数着心跳。医生说我的 resting heart rate 有点快,可能是因为药物,也可能是因为焦虑。但我喜欢数心跳,这是少数几个我能控制的节奏之一。它告诉我,是的,我还活着,尽管我不确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。有时候我会故意屏住呼吸,看看能坚持多久。不是自杀,真的不是,只是好奇,好奇那个临界点在哪里,好奇身体会在什么时候背叛我的意志,强制我重新开始呼吸。这种小小的叛逆让我感到一丝活力,仿佛在说:”看,至少我还能控制这个。”
手机又震动了,这次是闹钟——如果我每天中午12点之前起床,就能在日历上标记一个绿色的勾。这是我治疗师的建议,”建立积极反馈循环”。我看着那个闹钟,像看着一个恶意的玩笑。起床?为了什么?为了坐在沙发上发呆?为了用遥控器不停地换台却一个节目都看不进去?为了站在淋浴头下让水冲刷我却在里面哭到喘不过气?
但我还是动了。不是因为我想要那个绿色的勾,而是因为膀胱终于抗议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。这个动作像是一个连锁反应:坐起来,脚碰到冰凉的地板,站起来,眼前的黑点像烟花一样绽放,扶住墙,等待眩晕过去,然后是一步一步地挪向卫生间。
镜子。这个恶魔般的存在。我避免看镜子,但有时候它会突然出现在我的余光里,给我一个措手不及。镜子里的人是谁?那个眼睛浮肿、面色苍白、头发油腻的人是谁?它看起来像我,但又不完全是我。它看起来像一个失败品,像一个半成品,像一个被上帝遗忘在角落里的草稿。我快速移开视线,但那个影像已经烙在了视网膜上,像烧伤的疤痕。
水龙头流出的水太冷了,但我没有力气去调节温度。冰冷的水冲在手上,带来短暂的清醒。我盯着手看,这些血管,这些皱纹,这些指甲——它们都属于我,但它们看起来如此陌生。我把手举到灯光下,看着皮肤下的蓝色血管,想象着如果划开会怎样。不是计划,只是想象,就像想象如果中了彩票会怎样。这种想象带来一种奇怪的平静,仿佛在说:”看,你至少还有这个选择。”但我知道我不会真的去做,不是因为我害怕疼痛,而是因为我太疲惫了,连结束都嫌麻烦。
回到床上,我注意到床单上有新的污渍。可能是打翻的咖啡,也可能是汗水,或者眼泪——它们在我的生活中变得如此相似,都留下相似的痕迹。我应该换床单,但我没有干净的床单了。洗衣服需要把衣服放进洗衣机,加洗衣粉,按下按钮,然后等待,然后烘干,然后折叠——这个链条太长了,长到让我望而却步。我宁愿睡在污渍上,它们至少证明我还有一些功能,还能产生一些东西,哪怕只是体液。
下午三点,或者四点,时间开始变得模糊。我打开了电视,不是为了看,而是为了有声音填充这个空间。人声,音乐,笑声——这些应该让人愉悦的东西现在只是提醒我我失去了什么。我调到了一个烹饪节目,主持人用夸张的语气描述着一道我永远不会尝试的菜肴。他的热情看起来如此虚假,如此遥远,就像在看一个外星文明。我曾经也喜欢做饭,曾经也享受创造的过程。现在连微波炉加热剩菜都像攀登珠穆朗玛峰。
手机亮了一下,是社交媒体的通知。我本该避免这些,但像对待伤口一样,我总是忍不住要去揭开痂。是一个老朋友的婚礼照片,她看起来如此幸福,如此…正常。我放大照片,看着她的笑容,试图回忆起上一次我那样笑是什么时候。不是那种社交性的嘴角上扬,而是那种从肚子里升起来的、不受控制的、让脸颊发酸的真正的笑。我想不起来了。可能是在梦里,但连我的梦都变得灰暗,充满了追逐和坠落和永远找不到的出口。
我放下手机,感到一种奇怪的平静。不是那种积极的平静,而是风暴过后的废墟般的平静。我知道我不该比较,我知道每个人的战斗都不一样,我知道社交媒体是每个人生活的 highlight reel。但知道和感受是两回事。知道太阳是一颗恒星不会让你温暖,知道比较不好不会让你停止憎恨自己。
窗外的光开始变得金黄,然后橙色,然后消失。我没有开灯,让黑暗慢慢填满这个空间。黑暗是我的朋友,它不会问我问题,不会期待我表现,不会用”你应该”来压迫我。在黑暗中,我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,不再是一个失败的个体,而只是黑暗的一部分。这种匿名性带来解脱,就像一滴水回到海洋,终于不再是”一滴”。
我听着城市的噪音:汽车的鸣笛,邻居的音乐,楼上的脚步声。所有这些生命,所有这些活动,所有这些目的——它们在我周围旋转,而我固定在中心,像一个黑洞,吸收所有的光却不反射任何。这就是抑郁最残酷的部分之一:它不是让你哭泣或尖叫,而是让你变得透明,变成一个观察者而非参与者,变成生活这幅画上的一个污点,而非组成部分。
我想到S亡,不是作为一种愿望,而是作为一种概念。它看起来如此遥远,如此抽象,就像量子物理或古代历史。我知道有些人认为抑郁就是想S,但对我来说,它更像是已经S了,却还被迫要经历所有活着的仪式。呼吸,吃饭,睡觉,醒来——这些机械的动作失去了意义,变成了没有目的的例行公事。如果我现在死去,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不再需要假装这些动作有意义了。
但我不会S,至少今晚不会。不是因为希望,而是因为惯性。S亡需要计划和执行,而我连起床都困难。所以我就这样躺着,悬浮在生死之间的灰色地带,既不是完全活着,也不是完全死去。这种状态有一种奇怪的安全感,就像永远停留在机场的中转区——你不需要面对出发,也不需要面对到达。
夜深了,或者刚刚入夜,时间在我的公寓里变得柔软而可塑。我听着自己的呼吸,那种微弱的、不规则的、证明我还存在的证据。有时候我会想象如果呼吸停止会怎样,不是作为一种愿望,而是作为一种思想实验。但每次,身体都会背叛我的意志,继续这个无意识的机械动作。这种背叛让我感到一丝安慰——至少还有某个部分在为我战斗,即使那个部分只是脑干的最原始部分。
我闭上眼睛,不是为了睡觉,而是为了不再看。视觉需要解释,而解释需要能量。在黑暗中,我不需要看到污渍,不需要看到失败,不需要看到那个陌生的自己。我可以假装我是虚无,是空白,是尚未被写满的页面。这种假装带来短暂的解脱,就像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,至少有几秒钟的盲目。
但即使闭上眼睛,内心的眼睛仍然睁着,看着那个由记忆和恐惧组成的画廊。每一个失败,每一个遗憾,每一个”如果”——它们像幻灯片一样循环播放,没有暂停键,没有退出键。我试图用其他想法来分散注意力,但抑郁就像一块磁铁,吸引所有黑暗的东西,排斥任何光明的东西。这不是选择,这是化学,是神经递质,是大脑回路的故障,是我无法控制的生理过程。
我翻身到另一侧,床单发出轻微的沙沙声。这个声音在寂静中显得如此响亮,提醒我我的动作影响着这个世界,即使是最微小的方式。这种影响让我感到恐惧——如果我能产生声音,我是否也能产生其他影响?如果我存在,我是否也会伤害?这种连锁反应让我保持静止,尽量减少我的存在痕迹,仿佛这样就能减少我对世界的负面贡献。
凌晨时分,或者接近凌晨,天空开始变亮。这个时刻总是最艰难的——夜晚的承诺即将结束,白天的要求即将开始。我知道在几个小时内,我会听到邻居的闹钟,听到垃圾车的声音,听到这个世界重新启动的噪音。而我,将再次面临那个永恒的问题:起,还是不起?不是哈姆雷特的”生存还是毁灭”,而是更加基本的:”移动,还是继续躺在这里?”
我盯着那条天花板上的裂缝看。在黎明的光线中,它看起来不一样了,更像是一道伤痕,而不是微笑。我想到所有那些说”会好起来的”的人,他们的好意像绷带一样覆盖在开放性骨折上——善意,但完全不够。他们不会明白,”好起来”不是一条直线,而是一个迷宫,有死路,有回头路,有虚假的出口。他们不会明白,有时候”好起来”意味着学会与伤口共存,而不是等待它们愈合。
我闭上眼睛,不是为了睡觉,而是为了储存能量面对即将到来的战斗。不是与世界的战斗,而是与自己的战斗——与想要永远躺着的冲动,与想要消失的愿望,与那种认为自己不值得空气、空间、存在的信念的战斗。这场战斗没有观众,没有奖牌,没有终点线。只有我和我的影子,在拳击台的两边,永远对峙。
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,阳光已经完全穿透了窗帘。新的一天,或者同样的旧一天,取决于你看待时间的方式。我知道在某个时刻,我会再次数心跳,再次考虑呼吸,再次面对镜子里的陌生人。但在这一刻,在这一秒,我还躺在这里,存在于灰色地带,既不是胜利者,也不是失败者,只是一个…存在。
本篇 完
灵感来源:TB-SYSTEM/小纤(化名)
图片:TB-SYSTEM
文章:TB-SYSTEM/KimiAI
后期优化:TB-SYSTEM
其他TB-SYSTEM
献给我们班上的 小纤
无不良引导,仅科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