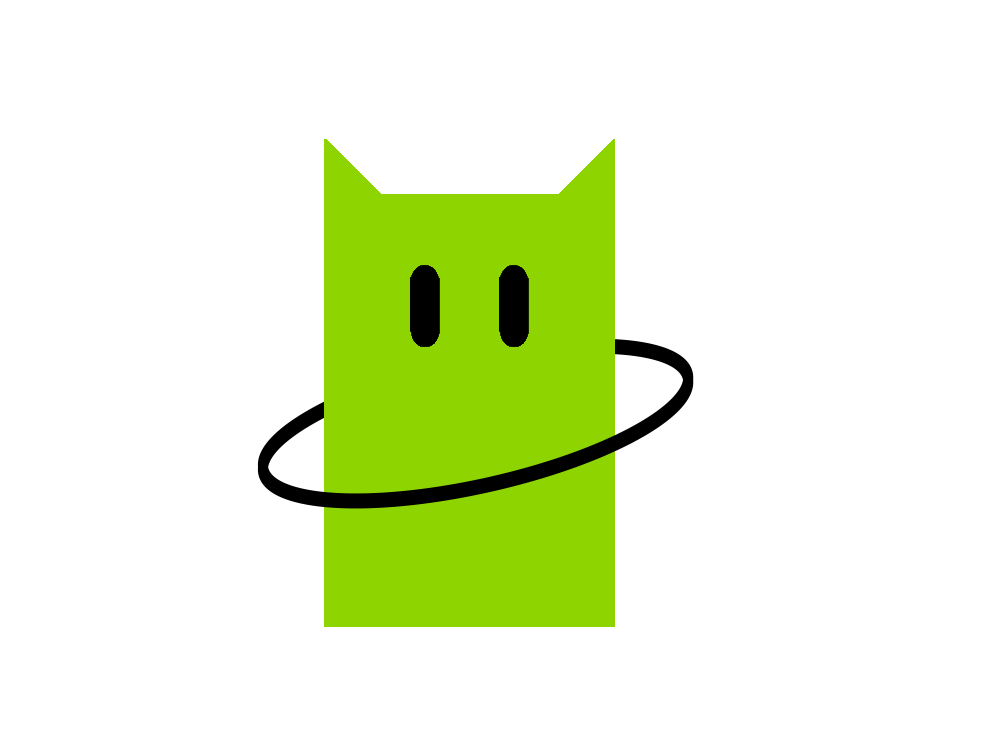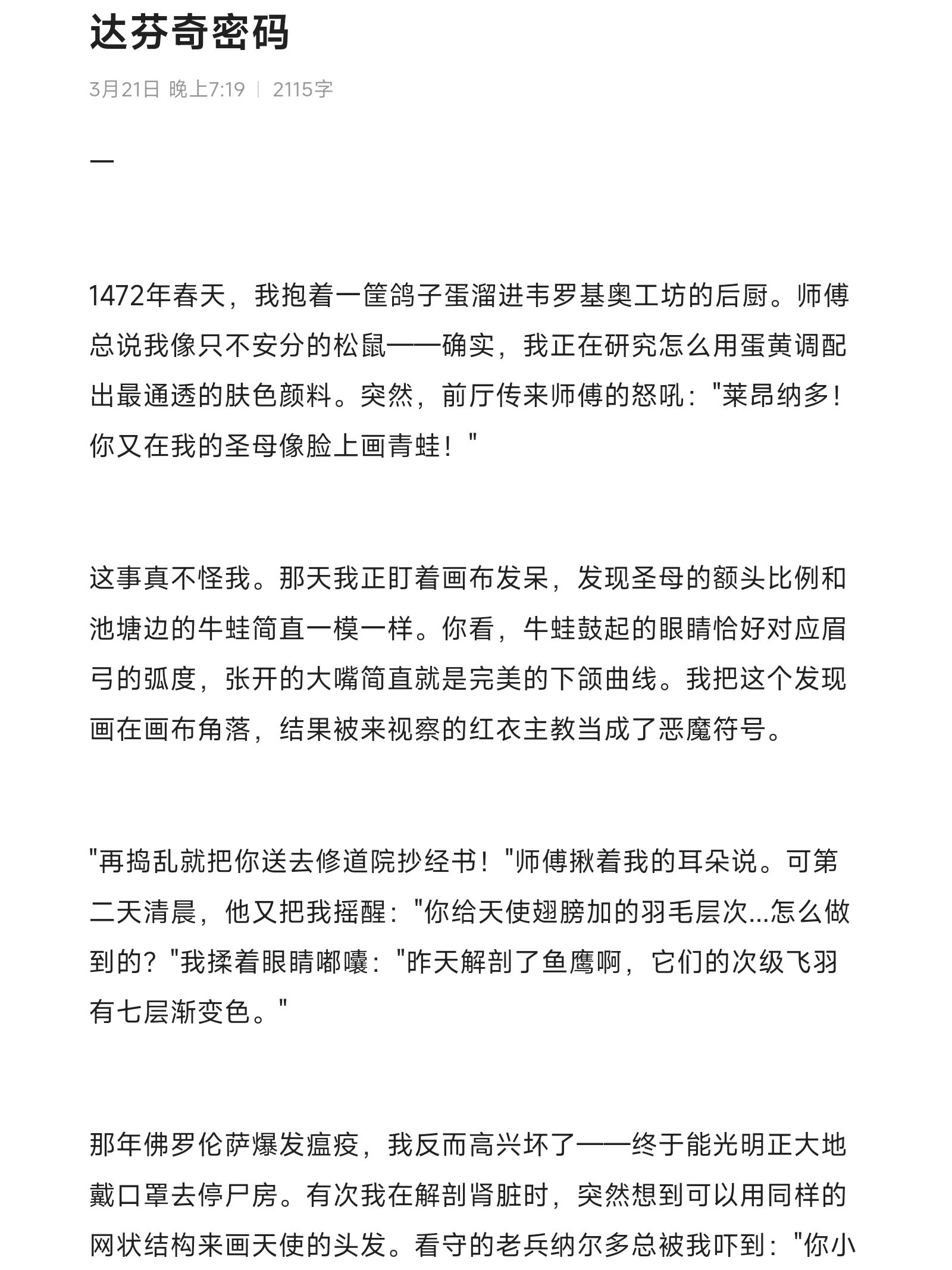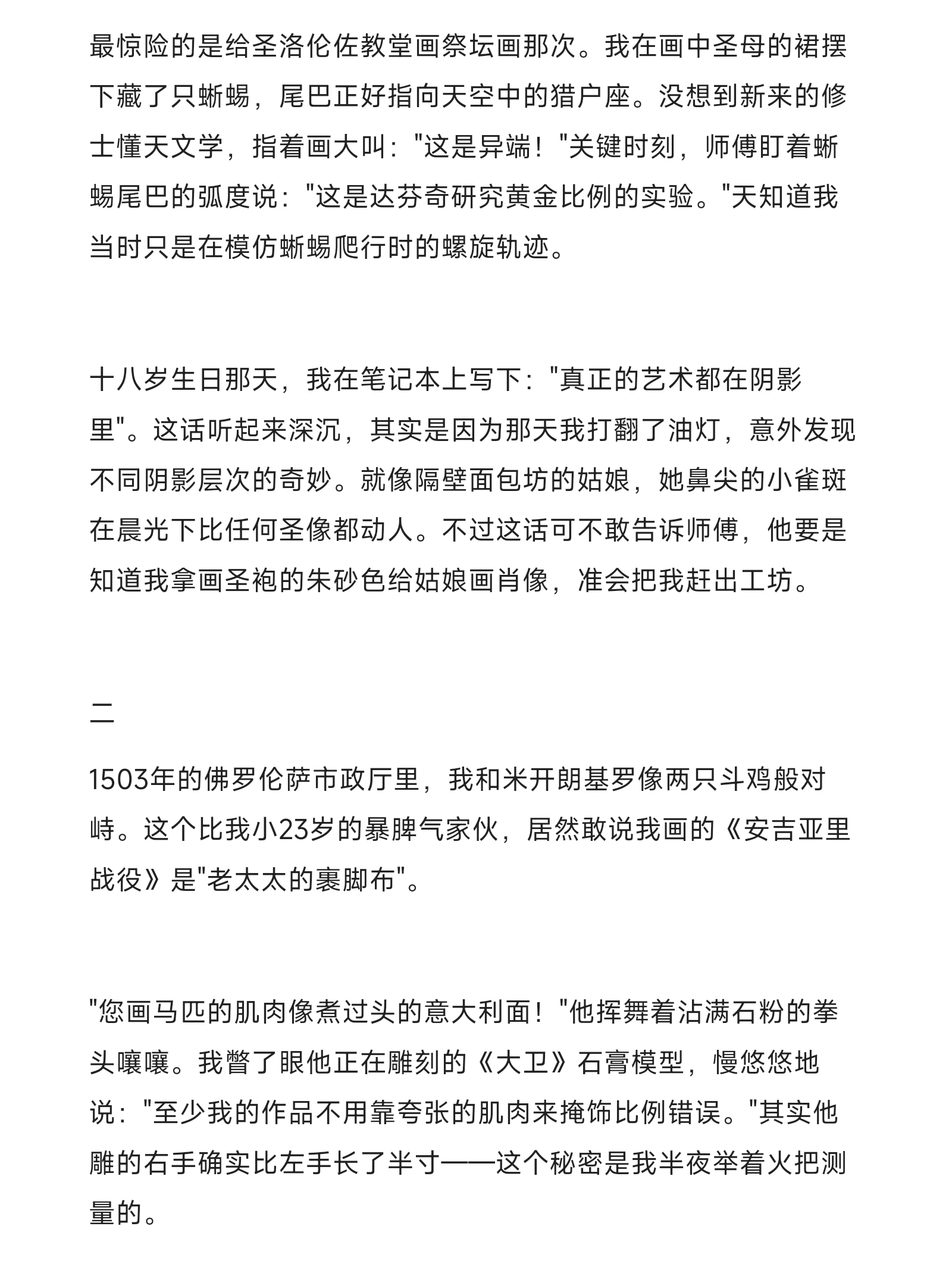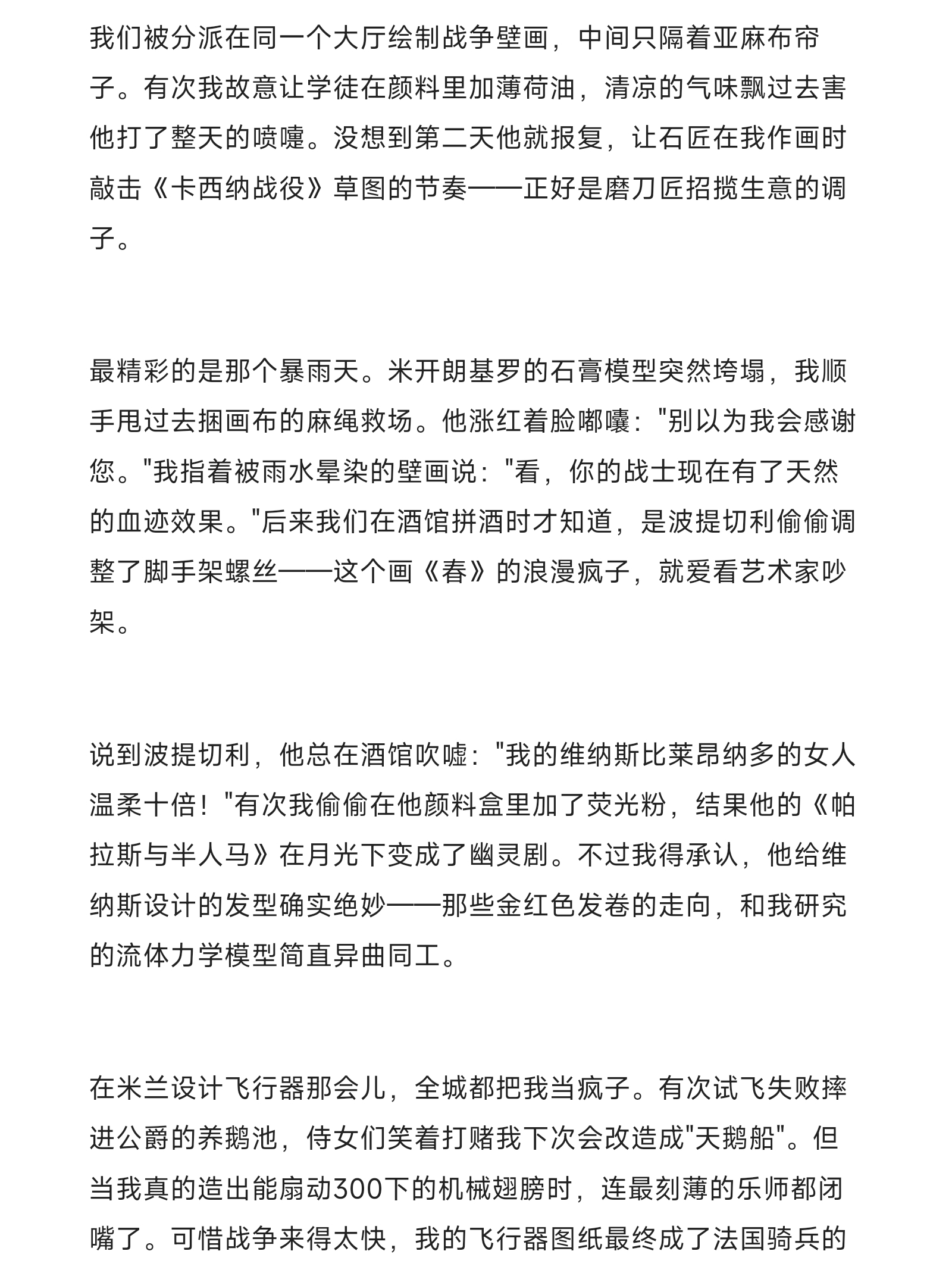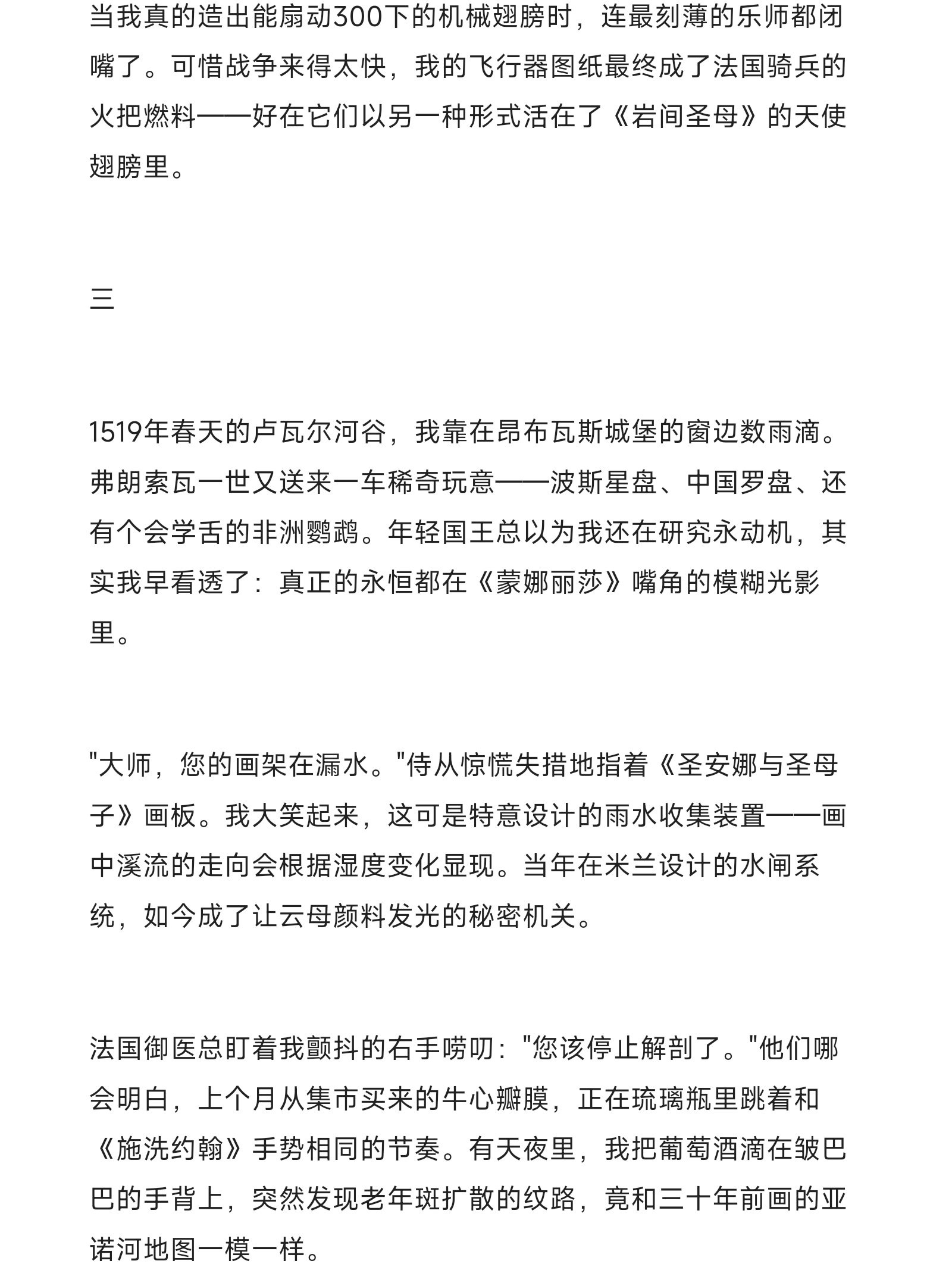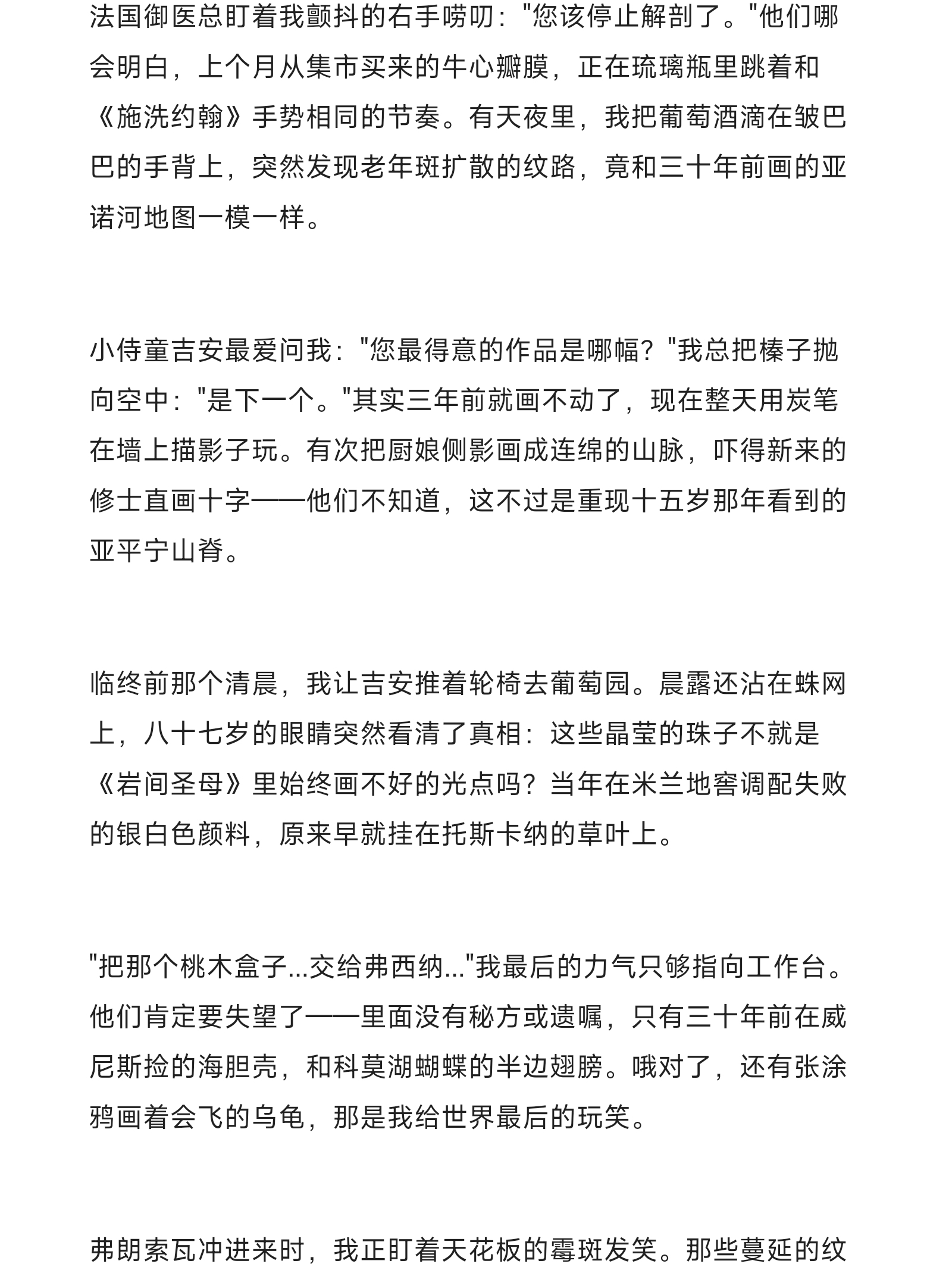一
1472年春天,我抱着一筐鸽子蛋溜进韦罗基奥工坊的后厨。师傅总说我像只不安分的松鼠——确实,我正在研究怎么用蛋黄调配出最通透的肤色颜料。突然,前厅传来师傅的怒吼:”莱昂纳多!你又在我的圣母像脸上画青蛙!”
这事真不怪我。那天我正盯着画布发呆,发现圣母的额头比例和池塘边的牛蛙简直一模一样。你看,牛蛙鼓起的眼睛恰好对应眉弓的弧度,张开的大嘴简直就是完美的下颌曲线。我把这个发现画在画布角落,结果被来视察的红衣主教当成了恶魔符号。
“再捣乱就把你送去修道院抄经书!”师傅揪着我的耳朵说。可第二天清晨,他又把我摇醒:”你给天使翅膀加的羽毛层次…怎么做到的?”我揉着眼睛嘟囔:”昨天解剖了鱼鹰啊,它们的次级飞羽有七层渐变色。”
那年佛罗伦萨爆发瘟疫,我反而高兴坏了——终于能光明正大地戴口罩去停尸房。有次我在解剖肾脏时,突然想到可以用同样的网状结构来画天使的头发。看守的老兵纳尔多总被我吓到:”你小子给尸体画速写的样子,比刽子手还瘆人!”
最惊险的是给圣洛伦佐教堂画祭坛画那次。我在画中圣母的裙摆下藏了只蜥蜴,尾巴正好指向天空中的猎户座。没想到新来的修士懂天文学,指着画大叫:”这是异端!”关键时刻,师傅盯着蜥蜴尾巴的弧度说:”这是达芬奇研究黄金比例的实验。”天知道我当时只是在模仿蜥蜴爬行时的螺旋轨迹。
十八岁生日那天,我在笔记本上写下:”真正的艺术都在阴影里”。这话听起来深沉,其实是因为那天我打翻了油灯,意外发现不同阴影层次的奇妙。就像隔壁面包坊的姑娘,她鼻尖的小雀斑在晨光下比任何圣像都动人。不过这话可不敢告诉师傅,他要是知道我拿画圣袍的朱砂色给姑娘画肖像,准会把我赶出工坊。
二
1503年的佛罗伦萨市政厅里,我和米开朗基罗像两只斗鸡般对峙。这个比我小23岁的暴脾气家伙,居然敢说我画的《安吉亚里战役》是”老太太的裹脚布”。
“您画马匹的肌肉像煮过头的意大利面!”他挥舞着沾满石粉的拳头嚷嚷。我瞥了眼他正在雕刻的《大卫》石膏模型,慢悠悠地说:”至少我的作品不用靠夸张的肌肉来掩饰比例错误。”其实他雕的右手确实比左手长了半寸——这个秘密是我半夜举着火把测量的。
我们被分派在同一个大厅绘制战争壁画,中间只隔着亚麻布帘子。有次我故意让学徒在颜料里加薄荷油,清凉的气味飘过去害他打了整天的喷嚏。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报复,让石匠在我作画时敲击《卡西纳战役》草图的节奏——正好是磨刀匠招揽生意的调子。
最精彩的是那个暴雨天。米开朗基罗的石膏模型突然垮塌,我顺手甩过去捆画布的麻绳救场。他涨红着脸嘟囔:”别以为我会感谢您。”我指着被雨水晕染的壁画说:”看,你的战士现在有了天然的血迹效果。”后来我们在酒馆拼酒时才知道,是波提切利偷偷调整了脚手架螺丝——这个画《春》的浪漫疯子,就爱看艺术家吵架。
说到波提切利,他总在酒馆吹嘘:”我的维纳斯比莱昂纳多的女人温柔十倍!”有次我偷偷在他颜料盒里加了荧光粉,结果他的《帕拉斯与半人马》在月光下变成了幽灵剧。不过我得承认,他给维纳斯设计的发型确实绝妙——那些金红色发卷的走向,和我研究的流体力学模型简直异曲同工。
在米兰设计飞行器那会儿,全城都把我当疯子。有次试飞失败摔进公爵的养鹅池,侍女们笑着打赌我下次会改造成”天鹅船”。但当我真的造出能扇动300下的机械翅膀时,连最刻薄的乐师都闭嘴了。可惜战争来得太快,我的飞行器图纸最终成了法国骑兵的火把燃料——好在它们以另一种形式活在了《岩间圣母》的天使翅膀里。
三
1519年春天的卢瓦尔河谷,我靠在昂布瓦斯城堡的窗边数雨滴。弗朗索瓦一世又送来一车稀奇玩意——波斯星盘、中国罗盘、还有个会学舌的非洲鹦鹉。年轻国王总以为我还在研究永动机,其实我早看透了:真正的永恒都在《蒙娜丽莎》嘴角的模糊光影里。
“大师,您的画架在漏水。”侍从惊慌失措地指着《圣安娜与圣母子》画板。我大笑起来,这可是特意设计的雨水收集装置——画中溪流的走向会根据湿度变化显现。当年在米兰设计的水闸系统,如今成了让云母颜料发光的秘密机关。
法国御医总盯着我颤抖的右手唠叨:”您该停止解剖了。”他们哪会明白,上个月从集市买来的牛心瓣膜,正在琉璃瓶里跳着和《施洗约翰》手势相同的节奏。有天夜里,我把葡萄酒滴在皱巴巴的手背上,突然发现老年斑扩散的纹路,竟和三十年前画的亚诺河地图一模一样。
小侍童吉安最爱问我:”您最得意的作品是哪幅?”我总把榛子抛向空中:”是下一个。”其实三年前就画不动了,现在整天用炭笔在墙上描影子玩。有次把厨娘侧影画成连绵的山脉,吓得新来的修士直画十字——他们不知道,这不过是重现十五岁那年看到的亚平宁山脊。
临终前那个清晨,我让吉安推着轮椅去葡萄园。晨露还沾在蛛网上,八十七岁的眼睛突然看清了真相:这些晶莹的珠子不就是《岩间圣母》里始终画不好的光点吗?当年在米兰地窖调配失败的银白色颜料,原来早就挂在托斯卡纳的草叶上。
“把那个桃木盒子…交给弗西纳…”我最后的力气只够指向工作台。他们肯定要失望了——里面没有秘方或遗嘱,只有三十年前在威尼斯捡的海胆壳,和科莫湖蝴蝶的半边翅膀。哦对了,还有张涂鸦画着会飞的乌龟,那是我给世界最后的玩笑。
弗朗索瓦冲进来时,我正盯着天花板的霉斑发笑。那些蔓延的纹路多像未完成的《安吉亚里战役》,或者说,像所有人生来就带着的草图。最后的意识停留在十五岁那个偷尸体的雨夜,当解剖刀划开胸腔时,我看到的不是器官,而是万千星河在血肉中流淌。
(传记·达芬奇篇 完)
后记:达芬奇去世时床前真的摆着海胆壳与蝴蝶翅膀(据同时代学者梅尔齐记载),他最后提到的弗西纳是跟隨四十年的仆人。《施洗约翰》现存卢浮宫,画中光影效果确实会随湿度变化产生微妙的流动感。
参考:①和达芬奇同时代有一位叫瓦萨里的老哥,写了本书叫《艺苑名人传》,本文有许多内容参考于此~如果有机会可以找来看一看੭ ᐕ)੭*⁾⁾②B站有一位叫“顾爷”的艺术讲解类up,讲的不错,如果有时间的话,推荐去看一看ヾ(✿゚▽゚)ノ
文/必刷禵原创